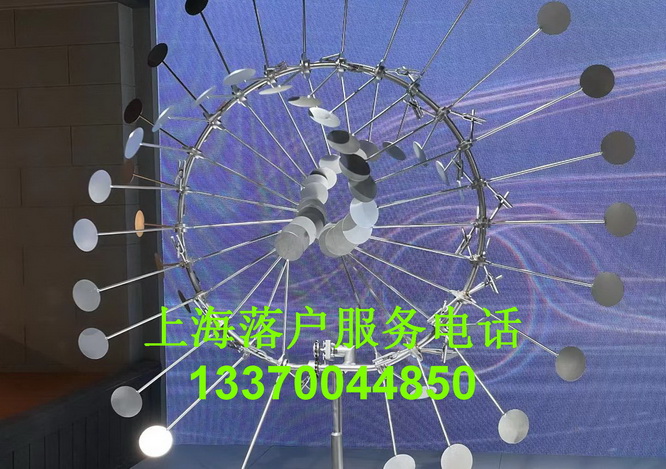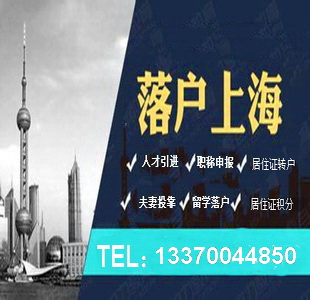儿行千里"收到喜帖了,郑光明,你看看。"我颤抖着声音,将那精致的红色请柬递给隔壁的老郑。六十五岁的我,姓李名振国,东北一所普通中学的退休语文教师。倚在我家那张陪伴了三十多年的老藤椅上,我望着手中这张来自上海的红色喜帖,只觉得眼前发黑。"振国,恭喜啊!小建终于要成家了。"郑光明接过喜帖,"上海姑娘?那可是好事啊!"老郑是我从小到大的邻居,也是为数不多能听我倾诉的知己。"好个屁!"我忍不住爆了粗口,指着喜帖最下方那行小字,"你瞧这,婚后男方随女方落户上海,入赘谢家!"那一瞬间,我六十五年的人生如走马灯般在眼前闪过,五味杂陈涌上心头。喜帖上印着的,是我的独子李建华和上海姑娘谢雅芳的婚礼邀请。"嗨,现在年轻人不都这样嘛,城市户口值钱。"老郑拍拍我的肩膀,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的理解。我摇摇头,一口气闷在胸口,说不出话来。"振国啊,想开点。"老郑递给我一根烟,"记得当初你省吃俭用送小建去上大学,不就是盼着他有出息、有好日子过吗?"我颤抖着点燃香烟,浓烟呛得眼泪直流。究竟是烟太呛人,还是心太痛 ?我自己也分不清了。一九八九年,李建华四岁那年,他娘因白血病离世。那时候,我刚从师范学院毕业不久,是县城中学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月工资只有四十八块钱。单位分了两间平房,砖墙水泥地,冬天寒风从窗缝灌进来,冷得直打颤。为了省钱给儿子攒学费,我连一个电热水器都舍不得买,每到冬天,都是烧一大锅开水,掺了凉水给孩子洗澡。记得他上小学那年冬天,东北的寒风刺骨,气温达到了零下三十多度。"振国,你这棉袄都几年了?领子都磨破了。"学校里的马老师看着我的衣服,关切地问。"还能穿呢,不碍事。"我笑着回应,却把攒下的工资给儿子买了一件崭新的羽绒服。当时羽绒服可是稀罕物,县城就那么一家国营商店卖,一件就要一百多块,几乎是我两个月的工资。"爸,你的棉袄都露棉花了。"小小的李建华拉着我的袖子说,黑葡萄似的眼睛里满是心疼。"爸不冷,爸身体壮。"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头,"你好好学习,将来就有钱给爸买新棉袄了。"那时的李建华多懂事啊,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台上海牌二八自行车和一台黑白电视机,那电视还是单位福利分的。每到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时间,邻居们都会挤到我家的小客厅,一群人围着那个十四寸的小屏幕,吃着瓜子闲聊。李建华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看书,从不打扰大人们。我省下钱给他买了一盏台灯,绿色的灯罩,带个小抽屉的那种。每晚都能看到他在昏黄的灯光下认真做作业的背影。"爸,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发明很多东西,让咱家富起来。"李建华经常这样对我说,眼睛里闪烁着孩子特有的纯真与坚定。为了这个朴素的梦想,我省下了所有能省的钱。我不抽名烟,不喝好酒,连袜子破了都是自己缝补。邻居们都说:"李老师这是活受罪哩!"我却笑着说:"不算啥,孩子他娘走得早,我得替她好好照顾孩子不是?"每到寒暑假,我就到补习班兼职,多挣点钱给李建华买课外书。那时候好书难求,县城新华书店的畅销书总是供不应求。每次进了新书,我都是第一个冲到书店,给儿子买回《十万个为什么》《少年百科全书》之类的读物。九十年代中期,县城掀起了第一波下岗潮。虽然作为教师我的工作还算稳定,但周围不少人家都陷入了困境。李建华上初中那年,邻居王大娘的儿子下岗了,一家人顿时断了经济来源。李建华知道后,主动把自己攒的零花钱塞给了王大娘家的小孙子。"爸,我不需要那么多零花钱,他们家比我们更需要。"他如此解释。那一刻,我眼眶湿润了,心想我这个儿子,真是长大了。高考那年,学校老师都说李建华有望考重点大学。我更加卖力地工作,连周末都到处补课挣钱。夏天的教室里没有电扇,我常常一边讲课一边用草扇子扇风,衬衫都能湿透了贴在背上。李建华以全市第三的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那一天,我第一次在同事面前流下了男儿泪,那是骄傲的泪水。送他去哈尔滨报到的路上,我把自己的积蓄都塞给了他:"儿子,爸就这些了,你别舍不得花,好好学习。"他接过钱,眼圈红了:"爸,等我毕业工作了,一定让您过上好日子。"那一年,县城的夜市开始热闹起来,大街小巷流行起卡拉OK。我却从不去凑这个热闹,一分一厘都要精打细算供儿子上学。可是,命运总喜欢和人开玩笑。大学第三年,李建华来电话说想考研究生,去上海。"爸,上海机会多,我想去闯一闯。"电话那头,李建华的声音充满了向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吧,爸支持你。"那年,我五十八岁,把自己的退休金和多年积蓄一次性给了他两万块,供他考研。老郑劝我:"振国啊,留点养老钱不好吗?儿子大学毕业能找到工作,干嘛非得继续念书?"我却说:"孩子有志气,我得支持啊。再说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再干几年,不怕。"那年冬天,我的膝盖落下了老毛病,关节痛得厉害。医生让我休息,我却不敢停下来。白天在学校给学生上课,晚上到补习班带学生,周末还接家教。一个月下来,膝盖疼得我走路都一瘸一拐的。老郑看不下去了:"你这是何必呢?伤了身子,谁照顾你?"我苦笑道:"不出意外,儿子这辈子就靠这一把了。"李建华没让我失望,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看着他背着行李离开的背影,我心里既骄傲又酸楚。我知道,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千里之遥。为了省钱,我一直没有安装座机电话,只能到邮电局打长途给儿子。每次排队等候的时间里,我都会仔细列好要说的话,毕竟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能浪费每一分钱。"爸,上海真好啊!这里的高楼大厦,地铁,还有各种美食..."他每次电话里都兴奋地描述着上海的繁华。"好就行,好好学习,别贪玩。"我总是这样叮嘱他。研究生毕业后,李建华留在了上海工作。起初,他每逢春节都会回家,带着各种上海特产——大白兔奶糖、小绒玩具、名牌香烟。"爸,这是今年上海最流行的烟,您尝尝。"他递给我一盒精致的香烟。我笑着接过,却从不舍得抽,一直放在柜子里,当做宝贝似的收着。慢慢地,他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电话也越来越简短。每次通话不超过五分钟,大部分时间都在说"工作忙""上海生活节奏快"之类的话。我清楚地记得,我退休那年,他竟然没有回来。"爸,实在抽不开身,公司有个大项目,我走不开。"电话那头,他的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歉意。我强装轻松:"没事,爸理解。你工作要紧,别为这个耽误了。"可挂了电话,我却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坐了一整晚,看着墙上他的照片发呆。从他小学毕业的合影,到大学录取的单人照,再到研究生毕
?我自己也分不清了。一九八九年,李建华四岁那年,他娘因白血病离世。那时候,我刚从师范学院毕业不久,是县城中学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月工资只有四十八块钱。单位分了两间平房,砖墙水泥地,冬天寒风从窗缝灌进来,冷得直打颤。为了省钱给儿子攒学费,我连一个电热水器都舍不得买,每到冬天,都是烧一大锅开水,掺了凉水给孩子洗澡。记得他上小学那年冬天,东北的寒风刺骨,气温达到了零下三十多度。"振国,你这棉袄都几年了?领子都磨破了。"学校里的马老师看着我的衣服,关切地问。"还能穿呢,不碍事。"我笑着回应,却把攒下的工资给儿子买了一件崭新的羽绒服。当时羽绒服可是稀罕物,县城就那么一家国营商店卖,一件就要一百多块,几乎是我两个月的工资。"爸,你的棉袄都露棉花了。"小小的李建华拉着我的袖子说,黑葡萄似的眼睛里满是心疼。"爸不冷,爸身体壮。"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头,"你好好学习,将来就有钱给爸买新棉袄了。"那时的李建华多懂事啊,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台上海牌二八自行车和一台黑白电视机,那电视还是单位福利分的。每到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时间,邻居们都会挤到我家的小客厅,一群人围着那个十四寸的小屏幕,吃着瓜子闲聊。李建华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看书,从不打扰大人们。我省下钱给他买了一盏台灯,绿色的灯罩,带个小抽屉的那种。每晚都能看到他在昏黄的灯光下认真做作业的背影。"爸,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发明很多东西,让咱家富起来。"李建华经常这样对我说,眼睛里闪烁着孩子特有的纯真与坚定。为了这个朴素的梦想,我省下了所有能省的钱。我不抽名烟,不喝好酒,连袜子破了都是自己缝补。邻居们都说:"李老师这是活受罪哩!"我却笑着说:"不算啥,孩子他娘走得早,我得替她好好照顾孩子不是?"每到寒暑假,我就到补习班兼职,多挣点钱给李建华买课外书。那时候好书难求,县城新华书店的畅销书总是供不应求。每次进了新书,我都是第一个冲到书店,给儿子买回《十万个为什么》《少年百科全书》之类的读物。九十年代中期,县城掀起了第一波下岗潮。虽然作为教师我的工作还算稳定,但周围不少人家都陷入了困境。李建华上初中那年,邻居王大娘的儿子下岗了,一家人顿时断了经济来源。李建华知道后,主动把自己攒的零花钱塞给了王大娘家的小孙子。"爸,我不需要那么多零花钱,他们家比我们更需要。"他如此解释。那一刻,我眼眶湿润了,心想我这个儿子,真是长大了。高考那年,学校老师都说李建华有望考重点大学。我更加卖力地工作,连周末都到处补课挣钱。夏天的教室里没有电扇,我常常一边讲课一边用草扇子扇风,衬衫都能湿透了贴在背上。李建华以全市第三的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那一天,我第一次在同事面前流下了男儿泪,那是骄傲的泪水。送他去哈尔滨报到的路上,我把自己的积蓄都塞给了他:"儿子,爸就这些了,你别舍不得花,好好学习。"他接过钱,眼圈红了:"爸,等我毕业工作了,一定让您过上好日子。"那一年,县城的夜市开始热闹起来,大街小巷流行起卡拉OK。我却从不去凑这个热闹,一分一厘都要精打细算供儿子上学。可是,命运总喜欢和人开玩笑。大学第三年,李建华来电话说想考研究生,去上海。"爸,上海机会多,我想去闯一闯。"电话那头,李建华的声音充满了向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吧,爸支持你。"那年,我五十八岁,把自己的退休金和多年积蓄一次性给了他两万块,供他考研。老郑劝我:"振国啊,留点养老钱不好吗?儿子大学毕业能找到工作,干嘛非得继续念书?"我却说:"孩子有志气,我得支持啊。再说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再干几年,不怕。"那年冬天,我的膝盖落下了老毛病,关节痛得厉害。医生让我休息,我却不敢停下来。白天在学校给学生上课,晚上到补习班带学生,周末还接家教。一个月下来,膝盖疼得我走路都一瘸一拐的。老郑看不下去了:"你这是何必呢?伤了身子,谁照顾你?"我苦笑道:"不出意外,儿子这辈子就靠这一把了。"李建华没让我失望,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看着他背着行李离开的背影,我心里既骄傲又酸楚。我知道,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千里之遥。为了省钱,我一直没有安装座机电话,只能到邮电局打长途给儿子。每次排队等候的时间里,我都会仔细列好要说的话,毕竟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能浪费每一分钱。"爸,上海真好啊!这里的高楼大厦,地铁,还有各种美食..."他每次电话里都兴奋地描述着上海的繁华。"好就行,好好学习,别贪玩。"我总是这样叮嘱他。研究生毕业后,李建华留在了上海工作。起初,他每逢春节都会回家,带着各种上海特产——大白兔奶糖、小绒玩具、名牌香烟。"爸,这是今年上海最流行的烟,您尝尝。"他递给我一盒精致的香烟。我笑着接过,却从不舍得抽,一直放在柜子里,当做宝贝似的收着。慢慢地,他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电话也越来越简短。每次通话不超过五分钟,大部分时间都在说"工作忙""上海生活节奏快"之类的话。我清楚地记得,我退休那年,他竟然没有回来。"爸,实在抽不开身,公司有个大项目,我走不开。"电话那头,他的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歉意。我强装轻松:"没事,爸理解。你工作要紧,别为这个耽误了。"可挂了电话,我却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坐了一整晚,看着墙上他的照片发呆。从他小学毕业的合影,到大学录取的单人照,再到研究生毕 业时我专门去上海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拍的合影。照片中的他,一张张脸庞渐渐成熟,眼神里的纯真却一点点消散。二零零五年,单位分房改革,我用积攒的钱加上公积金,总算在县城买了套六十平米的小两居。"爸,您那边条件还是太差了,要不要考虑来上海?我可以帮您在这边租房子。"李建华在电话里建议。"算了吧,我这把年纪了,习惯了东北的生活,去上海干什么?连话都说不利索。"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去年春节,他难得回来一次,却对我家的一切都流露出不习惯。他皱着眉头抱怨热水器太小,卫生间没有浴霸,家里wifi信号差,床太硬睡不习惯。"爸,您这房子太旧了,卫生间也没有热水器,冬天洗澡太难受了。""这不是从小住到大的吗?"我笑着回应,却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嫌弃。他带来一个新款手机送给我,说是方便我们视频聊天。可我这老花眼看不清那小屏幕,手指也不灵活,根本操作不了那复杂的功能。手机最终被搁在了抽屉里,积了厚厚的一层灰。那天晚上,我上厕所路过客厅,听到他在电话里对女友说:"别担心,就几天,忍忍就过去了。这里条件是差了点,但毕竟是我老家。"听到这话,我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一个月后,他发短信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对象是上海本地姑娘,家境殷实,父母都是某企业的高管。"爸,她叫谢雅芳,特别优秀,您一定会喜欢她的。"我只回了一句:"好,爸爸为你高兴。"婚礼那天,我穿上唯一一套还算体面的西装,独自一人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了上海。火车上,我紧紧攥着给儿子准备的红包,里面装着我的全部积蓄——两万块钱。这在上海或许不算什么,但对我这个退休教师来说,已是倾囊相助。上海浦东的五星级酒店金碧辉煌,宾客如云,全是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人物。我这身老旧西装,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谢家父母待我还算客气,但眼神中的轻视却掩饰不住。"李老师,您儿子真是不错,我们家小芳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我们就很满意。"谢父笑眯眯地说。"谢谢夸奖,建华从小就懂事。"我干巴巴地回答,不知该说什么好。酒席中途,李建华站起来宣布:"感谢各位的祝福。我和小芳商量好了,婚后我会迁户口到上海,入赘谢家。"全场掌声雷动,只有我的手僵在了半空中。他竟然事先都没和我商量过这么重要的决定。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儿子已经完全不在我的生活圈子里了。席间,我拉住李建华,问他:"儿子,你就这么决定了?连个商量都没有?""爸,上海机会多啊,谢叔叔还说要让我进入他们家的企业做管理层。"李建华有些不耐烦,像是在应付我。"那你以后姓什么?"我声音发颤,内心的不安变成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这不重要,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在乎这个?"他不以为然地回答,眼神飘向宴会厅另一边正在谈笑的谢家亲友。我和他争执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我不禁回想起当年他小学时立志要当科学家的单纯模样,如今却为了所谓的"更好生活",连根都不要了。谢家人围了过来,我看到李建华眼中的尴尬和焦急。"爸,您小声点,别在这里..."他压低声音,近乎哀求地看着我。我愣住了,突然觉得无比疲惫。"建华,你妈要是在天有灵,看到你这样,会怎么想?"我最终只能搬出他早逝的母亲。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扎进了他的心。李建华的眼圈红了,却没有再说什么。酒席后,谢家父母找到我,谢父语气温和却透着不容拒绝:"李老师,小建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我们家正好需要这样的人才。您就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吧,保证让他过上好日子。"谢母补充道:"李老师,您以后要是身体不好,也可以来上海养老,我们有专门的养老院资源。"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阵发凉。回到简陋的宾馆,我彻夜未眠。窗外的上海灯火辉煌,繁华似锦,那么美丽,那么遥远。东北的雪和上海的雨,到底哪个更能滋养一个人的根?我从行李中取出了一个旧皮夹,里面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李建华五岁生日时,我和他妻子抱着他的合影。那是我们全家唯一的一张合照。照片背面,是他母亲的遗言:"振国,好好把建华养大,盼他成才,莫要让他忘本。"我忽然明白,我倾尽所有培养起来的儿子,早已经不再属于我,也不再属于那个他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城。他被上海的繁华吸引,被物质的丰富诱惑,选择了一条我无法理解的路。可我能怪他吗?从他呱呱坠地那天起,我不就是希望他能过上比我好的生活吗?现在他有了自己的选择,我这个老头子又有什么资格阻拦?第二天一早,我提前退房,准备返程。李建华急匆匆赶来送我,脸上带着歉意。"爸,您别生气了。我这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他解释道,声音中带着几分愧疚。火车站的人流熙熙攘攘,背景是上海高耸的摩天大楼。看着儿子的脸,我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立志要当科学家的小男孩。我曾经以为,让他读书是为了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却没想到,教育竟让我们之间有了隔阂。"建华,你还记得你小学三年级时的那场朗诵比赛吗?"我突然问道。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记得,我朗诵的是《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得了第一名。爸,您还专门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奖励我。""对,就是那次。"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这是你妈留给你的,本想等你大学毕业给你的,后来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盒子里是一枚玉质的印章,上面刻着"李"字。"这是你外公亲手刻的,你妈临走前托付给我,说要等你长大成人了给你。"李建华接过印章,手微微颤抖。"建华,你记住,无论你姓什么,住在哪里,都改变不了你是我李振国的儿子这个事实。"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吧,爸爸尊重你的选择。"他紧紧抱住我,眼泪无声地流下。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看到成年后的他流泪。"爸,我..."他哽咽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口。"行了,别惹人注目。"我轻轻推开他,"好好珍惜你的幸福,别辜负了谢家的期望。"火车缓缓启动,我透过车窗,看到李建华站在站台上,手里紧握着那枚印章,眼神复杂地目送我远去。回到东北家中,我又回到了往常的生活轨迹。每天早晨在小区的空地上打太极拳,中午和老郑下几盘象棋,傍晚在附近的小学做义务家教。看着那些和当年李建华一样求知若渴的眼睛,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读书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为了忘记自己是谁。"一个月后,李建华突然打来电话,语气中带着兴奋:"爸,我和谢叔叔谈了,决定保留我原来的姓。他们全家都同意了!"我沉默了片刻,问道:"是你自己的决定吗?""是的,爸。那天您走后,我一直在想您给我的那枚印章。我意识到,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您的儿子,是东北人的儿子。"听到这话,我的鼻子一酸,却故作平静:"嗯,挺好的。你自己做决定就行,爸爸支持你。"挂了电话,我拿出那张全家福,轻轻抚摸着上面妻子和儿子的脸。"老伴啊,你看到了吗?咱们的儿子,终究没有忘本啊。"我对着照片喃喃自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两个月后,我收到一封特快专递,里面是一张去上海的机票和一封信。信中,李建华写道:"爸,我和雅芳商量好了,想请您来上海住一段时间。您放心,我们租了一套独立的小公寓给您,就在我家附近。您可以看看上海,也让我有机会好好尽尽孝道。"我看着信笑了,心想:六十五岁了,我终于明白,我倾尽所有养大的研究生儿子,虽然身在上海,娶了上海媳妇,但他的根,始终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可能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让他读书,让他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有勇气坚守自己的根。从窗外望去,东北的春天来了,院子里的老槐树抽出了新芽。我决定收拾行李,去上海看看。不为别的,就为了告诉儿子:无论他飞得多高,多远,家,永远是他的起点和归处。
业时我专门去上海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拍的合影。照片中的他,一张张脸庞渐渐成熟,眼神里的纯真却一点点消散。二零零五年,单位分房改革,我用积攒的钱加上公积金,总算在县城买了套六十平米的小两居。"爸,您那边条件还是太差了,要不要考虑来上海?我可以帮您在这边租房子。"李建华在电话里建议。"算了吧,我这把年纪了,习惯了东北的生活,去上海干什么?连话都说不利索。"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去年春节,他难得回来一次,却对我家的一切都流露出不习惯。他皱着眉头抱怨热水器太小,卫生间没有浴霸,家里wifi信号差,床太硬睡不习惯。"爸,您这房子太旧了,卫生间也没有热水器,冬天洗澡太难受了。""这不是从小住到大的吗?"我笑着回应,却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嫌弃。他带来一个新款手机送给我,说是方便我们视频聊天。可我这老花眼看不清那小屏幕,手指也不灵活,根本操作不了那复杂的功能。手机最终被搁在了抽屉里,积了厚厚的一层灰。那天晚上,我上厕所路过客厅,听到他在电话里对女友说:"别担心,就几天,忍忍就过去了。这里条件是差了点,但毕竟是我老家。"听到这话,我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一个月后,他发短信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对象是上海本地姑娘,家境殷实,父母都是某企业的高管。"爸,她叫谢雅芳,特别优秀,您一定会喜欢她的。"我只回了一句:"好,爸爸为你高兴。"婚礼那天,我穿上唯一一套还算体面的西装,独自一人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了上海。火车上,我紧紧攥着给儿子准备的红包,里面装着我的全部积蓄——两万块钱。这在上海或许不算什么,但对我这个退休教师来说,已是倾囊相助。上海浦东的五星级酒店金碧辉煌,宾客如云,全是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人物。我这身老旧西装,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谢家父母待我还算客气,但眼神中的轻视却掩饰不住。"李老师,您儿子真是不错,我们家小芳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我们就很满意。"谢父笑眯眯地说。"谢谢夸奖,建华从小就懂事。"我干巴巴地回答,不知该说什么好。酒席中途,李建华站起来宣布:"感谢各位的祝福。我和小芳商量好了,婚后我会迁户口到上海,入赘谢家。"全场掌声雷动,只有我的手僵在了半空中。他竟然事先都没和我商量过这么重要的决定。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儿子已经完全不在我的生活圈子里了。席间,我拉住李建华,问他:"儿子,你就这么决定了?连个商量都没有?""爸,上海机会多啊,谢叔叔还说要让我进入他们家的企业做管理层。"李建华有些不耐烦,像是在应付我。"那你以后姓什么?"我声音发颤,内心的不安变成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这不重要,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在乎这个?"他不以为然地回答,眼神飘向宴会厅另一边正在谈笑的谢家亲友。我和他争执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我不禁回想起当年他小学时立志要当科学家的单纯模样,如今却为了所谓的"更好生活",连根都不要了。谢家人围了过来,我看到李建华眼中的尴尬和焦急。"爸,您小声点,别在这里..."他压低声音,近乎哀求地看着我。我愣住了,突然觉得无比疲惫。"建华,你妈要是在天有灵,看到你这样,会怎么想?"我最终只能搬出他早逝的母亲。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扎进了他的心。李建华的眼圈红了,却没有再说什么。酒席后,谢家父母找到我,谢父语气温和却透着不容拒绝:"李老师,小建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我们家正好需要这样的人才。您就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吧,保证让他过上好日子。"谢母补充道:"李老师,您以后要是身体不好,也可以来上海养老,我们有专门的养老院资源。"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阵发凉。回到简陋的宾馆,我彻夜未眠。窗外的上海灯火辉煌,繁华似锦,那么美丽,那么遥远。东北的雪和上海的雨,到底哪个更能滋养一个人的根?我从行李中取出了一个旧皮夹,里面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李建华五岁生日时,我和他妻子抱着他的合影。那是我们全家唯一的一张合照。照片背面,是他母亲的遗言:"振国,好好把建华养大,盼他成才,莫要让他忘本。"我忽然明白,我倾尽所有培养起来的儿子,早已经不再属于我,也不再属于那个他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城。他被上海的繁华吸引,被物质的丰富诱惑,选择了一条我无法理解的路。可我能怪他吗?从他呱呱坠地那天起,我不就是希望他能过上比我好的生活吗?现在他有了自己的选择,我这个老头子又有什么资格阻拦?第二天一早,我提前退房,准备返程。李建华急匆匆赶来送我,脸上带着歉意。"爸,您别生气了。我这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他解释道,声音中带着几分愧疚。火车站的人流熙熙攘攘,背景是上海高耸的摩天大楼。看着儿子的脸,我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立志要当科学家的小男孩。我曾经以为,让他读书是为了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却没想到,教育竟让我们之间有了隔阂。"建华,你还记得你小学三年级时的那场朗诵比赛吗?"我突然问道。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记得,我朗诵的是《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得了第一名。爸,您还专门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奖励我。""对,就是那次。"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这是你妈留给你的,本想等你大学毕业给你的,后来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盒子里是一枚玉质的印章,上面刻着"李"字。"这是你外公亲手刻的,你妈临走前托付给我,说要等你长大成人了给你。"李建华接过印章,手微微颤抖。"建华,你记住,无论你姓什么,住在哪里,都改变不了你是我李振国的儿子这个事实。"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吧,爸爸尊重你的选择。"他紧紧抱住我,眼泪无声地流下。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看到成年后的他流泪。"爸,我..."他哽咽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口。"行了,别惹人注目。"我轻轻推开他,"好好珍惜你的幸福,别辜负了谢家的期望。"火车缓缓启动,我透过车窗,看到李建华站在站台上,手里紧握着那枚印章,眼神复杂地目送我远去。回到东北家中,我又回到了往常的生活轨迹。每天早晨在小区的空地上打太极拳,中午和老郑下几盘象棋,傍晚在附近的小学做义务家教。看着那些和当年李建华一样求知若渴的眼睛,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读书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为了忘记自己是谁。"一个月后,李建华突然打来电话,语气中带着兴奋:"爸,我和谢叔叔谈了,决定保留我原来的姓。他们全家都同意了!"我沉默了片刻,问道:"是你自己的决定吗?""是的,爸。那天您走后,我一直在想您给我的那枚印章。我意识到,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您的儿子,是东北人的儿子。"听到这话,我的鼻子一酸,却故作平静:"嗯,挺好的。你自己做决定就行,爸爸支持你。"挂了电话,我拿出那张全家福,轻轻抚摸着上面妻子和儿子的脸。"老伴啊,你看到了吗?咱们的儿子,终究没有忘本啊。"我对着照片喃喃自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两个月后,我收到一封特快专递,里面是一张去上海的机票和一封信。信中,李建华写道:"爸,我和雅芳商量好了,想请您来上海住一段时间。您放心,我们租了一套独立的小公寓给您,就在我家附近。您可以看看上海,也让我有机会好好尽尽孝道。"我看着信笑了,心想:六十五岁了,我终于明白,我倾尽所有养大的研究生儿子,虽然身在上海,娶了上海媳妇,但他的根,始终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可能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让他读书,让他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有勇气坚守自己的根。从窗外望去,东北的春天来了,院子里的老槐树抽出了新芽。我决定收拾行李,去上海看看。不为别的,就为了告诉儿子:无论他飞得多高,多远,家,永远是他的起点和归处。
机构入驻
退出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