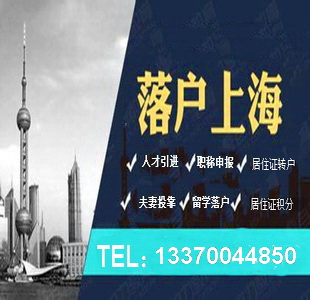多年以后,18岁的王伟涛同样坐上了这列火车,只是火车开往的方向,是父辈心之向往的上海。& 我是被我爸妈推上火车的。&王伟涛说,& 上海对我来说不是家,我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归属。那是他们的梦,不是我的。&
王伟涛的爷爷是在上世纪60年代拖家带口到甘肃支援大西北的上海人。四十多年来,一家人始终说着上海话,盼着有一天能回家。
成年以后,王伟涛考上大学,带着父辈的心愿离开甘肃回到上海,在杨浦的长阳谷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有得卖&。
& 在甘肃,大家都觉得家不在那里,总有一天要回去的;如今回到了上海,却依然觉得自己是外地人。&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那个一直被恐怖阴影笼罩着的城市——白银。
阴影笼罩的工业城市
白银是在戈壁滩上开发出来的一个重工业城市。建国后,苏联在此建设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因矿而设厂,因厂而立市,1956年建成白银市。
上世纪60年代,和王伟涛的爷爷一样受国家开发大西北感召的人们,从东北、湖南、上海等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投身到灰蒙蒙的荒山之间,开掘矿山,建设城市。王伟涛是第三代厂矿子弟。
& 人们都来自不同地方,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工厂都有自己的方言,听人聊天,就能分辨出他来自哪个厂。&王伟涛回忆说,& 每个人都盼着回家,但回不去,父母那一代人除非放弃工作,否则回去也没法生活。&
白银很小,从南往北四公里,从东到西也不过十公里。& 在这个小城市里,没有老人,只有年轻人和小孩,每到寒暑假,家长都在上班,小区里全是孩子。&王伟涛说,& 居住的地方也是按照厂子分的,一个院子就是一个厂,连小朋友之间也都是按厂分的。&
& 你是884的?我是330的。&小朋友之间互相称呼彼此都会用工厂的代号,& 884是铜加工厂,做弹壳的;330是荧光厂,造火药的……&王伟涛还记得清楚。
在他眼里,白银一直是个被妖魔化了的城市。这座城市被杀人案的阴影笼罩了28年,时间久到足够一代厂矿工人老去,另一代人成长。
1998年,白银连续发生四宗命案的时候,王伟涛上高一。& 当时我们晚自习都不敢上,整个城市年满16岁的男性都要提取DNA,女孩子都不敢穿红衣服,因为传说穿红衣服会被犯人盯上。&
杀人阴影伴随的是这座工业城市的衰落。直到28年后,当疑凶被抓的新闻传来时,白银人都聚集到了大路上,他们兴奋地交谈,甚至放起了鞭炮。& 整个城市都解脱了。以前白银人很担心,万一抓不到怎么办,万一这个人死了怎么办……&王伟涛还记得白银那条布满槐树的公路,夏末秋初的天空,一定是异常的湛蓝。
回到陌生的& 故乡&
白银的西北部有一个火车站,每天清晨七点五十分,绿皮车的汽笛声准时响起,59年来,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进来,载着一代人的梦想离开。
王伟涛的爷爷原来在上海斜土路上经营着一家米铺,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米铺被收了,爷爷就响应号召坐上了到西北的火车。
& 绿皮火车出了上海以后就一路飞驰,越开越荒凉。四野空茫茫,戈壁滩上寸草不生,只有几点红柳和铃铛刺。想着这就是未来生活的地方,整个列车的人就开始哭。&来时的情景,王伟涛听爷爷说了一遍又一遍。
多年以后,18岁的王伟涛同样坐上了这列火车,只是火车开往的方向,是父辈心之向往的上海。& 我是被我爸妈推上火车的。&王伟涛说,& 上海对我来说不是家,我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归属。那是他们的梦,不是我的。&
2001年,西北师范大学毕业后,王伟涛独自来到上海找工作,和朋友在康健路上租了一间三居室,5个人住,每人分摊月租200元。
那一年,IT行业经历低谷期,读计算机专业的王伟涛面试了十几家公司都失败了。& 没有上海户口,连KFC都不要你。&每次面试后对方都让他回家等,等了一个晚上没有任何消息,他就第二天一早到公司问。& 可能是因为这份执着和渴望,最后一家只有4个人的小IT公司要了我。&
就这样当了一年多的程序员,王伟涛又换了另一家软件公司。& 这家公司有8个人,比原来的规模翻了一倍呢。&王伟涛笑言,& 很多人希望到大公司,但其实小公司能培养人‘以一顶十’的能力。&在新公司,王伟涛不再只是做没有技术含量的编程工作,而是开始独立完成项目,同时也学会了一些团队发展和企业管理的经验。
2009年,想自己出来做点事情的王伟涛和朋友合开了一家登山俱乐部,那是当时上海开出的第一批户外运动俱乐部。& 从2001年刚来上海时一个朋友都没有,到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到发现自己对摄影的兴趣,这一切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在上海创业的西北人
对摄影的兴趣,延伸到了做摄影器材二手交易的想法上,同一年,王伟涛自己创立了& 有得卖&这个品牌。
& 我们把二手电子产品变成一种‘货币’,通过这个平台进行交易流通,‘购买’新的产品。&王伟涛举了个例子,& 如果你是个‘果粉’,每次iPhone出新款时你都可以通过‘有得卖’获得最新款手机,而从iPhone5用到iPhone7,你只需要花不到一万元。&
初创时,公司只有几个人。& 我租了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几个人吃住都在一起。&一边经营着初创期的公司,一边过着自己买菜烧饭的日子,凭着西北人敢闯敢拼的劲儿,王伟涛度过了最困难的头几年。& 刚开始公司的人事、税务、财务我都不懂,水电煤和房租都是我自己去交的,那时候没有什么众创空间或孵化器。&
今年5月,王伟涛在位于上海杨浦长阳谷的& 启迪之星&创业孵化器重新注册了新公司。税收、财政、招人等事务,公司一百多人的住房问题等都一一得到解决。在创新创业的氛围下,& 有得卖&获得了40万元的市创新基金补贴。& 我是技术出身,过去管理业务分散了很多精力,现在可以专心做研发,经营自己的事业。&
父母也在几年前随儿子回到了上海。& 他们现在过得很幸福,退休在家,也不用再为我的事业操心,最重要的是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回家了。&但王伟涛说,父母一有空还是会往甘肃跑,毕竟朋友圈子都还在那边。
& 回&到上海15年了,王伟涛称自己为& 在上海创业的西北人&。西北大地的风沙,在这个黝黑壮实的中年男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刮沙尘暴,一看到天边开始变黄,就马上往家里跑,门一关上,沙尘暴就来了,打在窗户上砰砰直响。&那座黄沙漫天的城市,和沙尘中里的小房子,是王伟涛一直留恋的地方。
& 来到上海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他的印象里,上海还是那个小时候每年必定全家来一次的大都市。& 我还记得南京路的第一食品商店。每次来上海,爸妈总要到南京路逛街买东西,他们在那儿就给我买一个奶油蛋糕,让我在路口的小人书摊边吃边看书,花5分钱就能看一下午。在白银,我从来没吃过奶油蛋糕,那时觉得,这真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机构入驻
退出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