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认定事实
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系案外人吴某庚与黄某庚同生育的子女,吴某庚与黄某戊系夫妻关系。 李某甲与吴某乙于 2010 年 2 月 8 日登记结婚,吴某甲系李某甲与吴某乙于 2014 年 10 月 18 日生育的女儿。 黄某甲与吴某戊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登记结婚,吴某丙、吴某丁系黄某甲与吴某戊分别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2014 年 10 月 21 日生育的儿子。 户主为吴某庚。 上思县公安局某丁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出具的户籍证明载明:《1995 年以前思阳村加达屯》记载户主吴某庚,配偶黄某戊、长子吴某乙、次子吴某戊、三子吴某己。 1992 年吴某庚的户口因城镇增容农转非由思阳村迁到某庚。 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户口于 1994 年从北湖社区加达屯迁到上思县某公司 (户籍登记地为广西上思县思阳镇东湖社区吴某庚户)。 黄某戊的现户籍登记地在某己。 1990 年 11 月 18 日,某己与黄某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某己将 2.05 亩耕地发包给黄某癸。 黄某癸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上记载:发包方加达队,承包方黄某戊,登记人口数由 “4” 涂改为 “5”,劳动力 “2”,承包期限从 1990 年 11 月 8 日起至 1999 年 12 月 31 日止。 1998 年 12 月 10 日,加达生产队作为发包方 (甲方) 与黄某戊作为承包方 (乙方) 签订《农业承包补充合同书》,合同书约定:在甲乙双方原签订《农业承包合同书》的基础上,合同期满,水 (旱) 田、坡地再延长承包期三十年,即有效期再从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起延长至二〇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山地再延长承包期七十年,即有效期再从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起延长至二〇七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2018 年某己的集体土地被征收,黄某癸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的土地亦在征收范围。 2018 年某己于 2018 年 1 月 27 日讨论通过分配方案,该方案载明:一、为确保本屯某丙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通过全体村民会议商议决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村民方可享受本村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权利:(一) 户口关系:1. 户口在本屯的村民 (不包括外嫁女子女和空挂户);2. 户口不在本屯的非农户口可以享受本屯集体经济分配的有:李某乙、黄某丙、黄某丁等三户;(二) 婚姻关系:1. 与本屯村民结婚且户口迁入本村的;2. 与本屯村民结婚但户口未迁入本屯,需经本屯某丙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户代表同意的;(三) 其他将户口依法迁入本屯,并经本屯某丙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接纳为本屯某丙成员的。 二、属于以下条件的不可以享受本屯集体经济分配:1. 外嫁女户口在或不在本屯的子女 (外甥子女);2. 户口随母亲嫁入或者迁入本屯的子女 (外甥子女);3. 非本屯成员在本队买地皮建房的外屯人员。 某己共有 25 户,同意该方案的有 22 户。 2018 年以来,某己于 2018 年、2024 年、2024 年、2024 年、2024 年按每人 6800 元、500 元、4700 元、7300 元 (600 元 + 6700 元 + 500 元)、34000 元分配了集体收益。 2024 年 12 月 18 日,那琴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吴某庚已迁出那琴村,其在那琴村没有享受耕地补贴、粮食补贴、稻谷补贴,没有获得山水林某等集体权益。 一审法院到某戊调取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户籍随父母落户情况未果。
一审法庭审理过程中,吴某甲等人称黄某癸承包的土地在 2024 年已经被全部征收完毕。 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小时候在某己生活,后来陆续到县城居住就读。
一审诉讼请求
吴某甲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 确认吴某甲等人均享有某己某丙成员待遇;2. 某己向吴某甲等人支付集体收益 53800 元 / 人,吴某甲等人共计 430400 元;3. 案件受理费由某己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
能否取得集体收益的分配资格应当以是否具有某丙成员资格为前提。 关于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是否具有某己的某丙成员资格。 取得或者丧失某丙成员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户籍登记情况、生产生活状况、农村土地对当事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予以认定。 关于某丙成员资格的取得。 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的户籍在 1994 年前曾随父或母落户于某己,三人曾取得了某己的户籍;1990 年 11 月 8 日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所在的黄某癸曾经与某己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三人作为黄某癸的家庭成员,享有某己分配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依赖某己的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来源及保障,据此,可以认定吴某乙、吴某戊、吴某曾经具有某己某丙成员资格。 关于某丙成员资格的丧失。 首先,1994 年 4 月 1 日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户籍因 “农转非” 从某己随父亲迁入上思县某公司,三人因政策性的城市增容 “农转非” 户口由农村转为城镇;其次,2024 年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所在的黄某癸的承包地已全部被征收完毕,三人已不再以承包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最后,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长期未 在某己生产生活,未履行某丙成员义务。 综上,可以得知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的户籍已迁出某己,2024 年以后承包地被征收完毕,三人在某己的户籍及土地承包基础均已丧失,三人自 2024 年承包地被征收完毕之时丧失了某己某丙成员资格。 关于某己是否应支付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集体收益。 依前所述,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自 2024 年承包地被征收完毕之时丧失了某己某丙成员资格。 那么 2024 年之前三人作为某己的某丙成员,应当有资格参与集体收益的分配。 2024 年前,某己按人均 6800 元标准分配某己的集体收益,故某己应按照每人 6800 元集体收益款的标准支付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
在某己生产生活,未履行某丙成员义务。 综上,可以得知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的户籍已迁出某己,2024 年以后承包地被征收完毕,三人在某己的户籍及土地承包基础均已丧失,三人自 2024 年承包地被征收完毕之时丧失了某己某丙成员资格。 关于某己是否应支付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集体收益。 依前所述,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自 2024 年承包地被征收完毕之时丧失了某己某丙成员资格。 那么 2024 年之前三人作为某己的某丙成员,应当有资格参与集体收益的分配。 2024 年前,某己按人均 6800 元标准分配某己的集体收益,故某己应按照每人 6800 元集体收益款的标准支付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
关于李某甲、吴某甲、黄某甲、吴某丙、吴某丁是否具有某己某丙成员资格。 虽然李某甲系吴某乙的配偶、黄某甲系吴某戊的配偶,吴某甲系吴某乙的子女,吴某丙、吴某丁系吴某戊的子女,但李某甲、吴某甲、黄某甲、吴某丙、吴某丁均未落户于某己,也未分配承包地,故李某甲、吴某甲、黄某甲、吴某丙、吴某丁不能因为婚姻或出生而取得某己某丙成员资格,进而不能参与某己集体收益分配。
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一、某己支付吴某乙集体收益款 6800 元;二、某己支付吴某戊集体收益款 6800 元;三、某己支付吴某己集体收益款 6800 元;四、驳回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上诉情况
一审判决后,吴某甲等人上诉请求:一、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某己支付吴某乙集体收益款 53800 元;二、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某己支付吴某戊集体收益款 53800 元;三、改判一审判决第三项为某己支付吴某己集体收益款 53800 元;四、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五、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某己分别支付李某甲、吴某甲、黄某甲、吴某丙、吴某丁集体收益款各 53800 元;六、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某己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将李某乙、黄某丙、黄某丁等三家农户基本情况进行阐明。 一审法庭调查阶段上诉人向某己提问,根据某己诉讼代理人黄某丁的回答内容,可以得知李某乙、黄某丙、黄某丁等三家农户家庭成员均已农转非,户籍亦已不在原藉加达村民小组,且也已不在原户籍地即某己处居住。 该事实与认定某己村民资格和村民待遇相关,关系到八上诉人是否与这三家人一样还享有某己的村民待遇,分得某己的集体收益,一审判决未认定该部分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 二、开庭后,一审只调查上诉人所在农户 (户主黄某戊) 承包经营的土地已全部被征收的事实,而对某己其他农户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也已全部被征收的事实不予调查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 三、至 2024 年止,某己由本集体各农户承包的集体耕地因城镇建设规划需要已逐渐被全部征收,所有农户与吴某甲等人所在的农户一样丧失对原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大家均已成失地农民,享受国家统一待遇。 之后分配给各农户成员的集体收益均来自 2024 年前各个阶段土地被征收的补偿款。 根据法律规定,农村某丙的财产归该集体全体成员所有,即便是至 2024 年吴某甲等人所在农户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至少对此前集体财产即土地被征收应得的补偿收益亦应尚享有共同所有权,在分配该收益时亦应得到享受的待遇。 四、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因户籍曾在某己某丙同时还承包有某己土地而被确认为某己某丙成员,其与李某乙、黄某丙、黄某丁等人的情况完全相同,李某乙、黄某丙、黄某丁的配偶与子女都能得到某己集体收益分配,李某甲、吴某甲是吴某乙配偶和女儿,黄某甲、吴某丙、吴某丁是吴某戊的配偶和儿子应与李某乙、黄某丙、黄某丁的配偶和子女一样分得集体经济收益。某己辩称,一、吴某甲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某丙成员资格认定应以是否具有农业户口作为形式要件,以是否实际在本某丙生产生活、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本条件等为实质要件来进行判断。 吴某甲等人既不是农业户口,其户籍也自始不在某己,从来没有在某己生产生活,更没有以黄某戊的承包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 二、承包地否被征收与本案关于某丙成员的认定没有关联。 黄某戊的承包地即便没有被征收,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均不可能是加达村民小组某丙成员。 三、一审部分认定错误,让吴某甲等人造成错误认识。 1、一审认定 “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的户籍已迁出某己,2024 年以后承包地被征收完毕,三人在某己的户籍及土地承包基础均已丧失,三人自 2024 年承包地被征收完毕之时丧失了某己某丙成员资格” 错误。 (1) 该结论是经 “首先部分”、“其次部分”、“最后部分” 得出结论的。 其中,“首先部分” 是对形式要件评述,即是否具有农业户口;“最后部分” 是 “实际要件” 的评述,即是否长期在加达村民小组生产生活。 该两项内容就足以认定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自 1994 年后不再具有加达村民小组的某丙成员资格。 (2) 对于 “其次部分” 论述错误,因为在 2024 年,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均不在黄某癸,黄某癸只有黄某戊一人。 吴某甲等人加上吴某庚、黄某庚 10 人,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个家庭的人均在城镇中拥有工作,在所在社区缴纳社保,一审认为三人以承包地作为基础生活保障缺乏事实依据,且该内容对本案的身份认定不产生影响,法律对此没有规定,黄某戊的承包地是否被征收与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无关。某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并依法驳回吴某甲等人的诉讼请求或驳回吴某甲等人的起诉;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吴某甲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对于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是否具有某己某丙成员资格认定错误。 一、一审认定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曾经具有某己某丙成员资格证据不足且与本案其他证据均不相符。 1、仅依据《户籍证明》不足以认定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曾取得某己的户籍。 (1) 根据 1990 年 11 月 18 日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和某己二审提交的上思县思阳镇财政局 1994 年 7 月 4 日出具的《证件》记载,户主均是黄某戊;(2) 但《户籍证明》主文第二段《1995 年以前思阳村加达屯》记载户主是吴某庚;(3)《土地承包合同书》和《证件》的记载相比于某丁的单方面陈述更有证明力,在没有附件印证或者新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不应采纳某丁的单方面陈述,而否认《土地承包合同书》和《证件》的记载内容。 2、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在迁往上思县思阳镇东湖社区的户籍迁出地是那琴乡那琴村上伴屯。 户口簿与上思县某甲出具的《户籍证明》中关于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迁出地址的记载内容矛盾,前者记载户籍迁出地是那琴乡那琴村上伴屯,后者记载户籍迁出地是北湖社区加达屯。 从证据的效力上讲,前者是具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某户口专用章和上思县公安局户口专用章,后者仅是某丁的单方面陈述,而且《户籍证明》并没有相关的附件佐证,仅凭上思县某甲的单方面陈述,不能直接认定户口簿的记载内容错误。 二、一审关于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在其户籍在迁至上思县思阳镇东湖社区后,仍具有某己的某丙成员的认定不符合农村某丙成员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同时也违背上思县某乙办公室文件的精神。 1、对于某丙成员资格的认定,以是否具有农业户口作为形式要件,以是否实际在本某丙生产生活、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本条件等为实质要件来进行判断。 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的户籍不在某己,从形式要件上看不符合认定某丙成员资格的条件。 2、从实际要件上看,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将户籍迁至上思县思阳镇东湖社区的前后至今,自始至终从未在某己生活过,三人在其住所地均有稳定工作,生活来源明显不可能依靠本案黄某戊承包的 2.05 亩耕地,其缴纳的社会保险也均不在某己所在社区,三人与某己自始至终均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三人均不认识某己的村民,村民也从未见过三人,一审仅认为三人在 30 多年前曾落户在某己就认为其一直是某己的某丙成员错误。 3、退一步讲,从上思县某乙办公室文件《关于职工家属农转非后责任田问题的通知》[上政办 (1986) 7 号] 的精神也可以认定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在户籍迁至上思县思阳镇东湖社区后就已经丧失某己的成员资格。 上思县某乙办公室文件是地方性文件,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其规定的上述条件,只是临时保障在农转非后生活困难的问题,但绝不是一直可以保留在原某丙享有成员权利,否则,所有的农转非就是既享受城镇户口的福利,也享受农村某丙成员的权益,“两边占” 明显不可能。 三、某己在一审阶段提交《调查申请书》,一审没有批准,但如果调取该证据,可以直接否定黄某辛某己的某丙成员身份,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三人自然也不可能获得某己的某丙成员身份。 1、某己在一审阶段提交申请调查黄某戊是否取得吴某庚户 (或所在户) 所在地上思县那琴乡那琴村上伴屯某丙的承包地,享受吴某庚户 (或所在户) 所在某丙成员待遇,一审未予批准调查,但同一村民不可能在两个某丙享受权益,在黄某戊外嫁后,如果享受其配偶吴某庚所在地 “那琴乡那琴村上伴屯” 的分配了承包地等村民权利就已失去某己的某丙成员资格。 2、一审调取的那琴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其内容只提及吴某辛住址是那琴村上伴屯 67 号已迁出,没有提及迁出时间。 其陈述吴某庚 “没有获得山水林某等集体权益” 的陈述不符合历史事实,理由如下:(1) 黄某戊和吴某庚结婚时间是 1978 年左右,结婚后不久 1982 年,全国就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此时吴某壬黄某戊的地址是 “那琴村上伴屯 67 号”,在那琴村上伴屯肯定按人口分配承包地等村民权益。 (2) 根据户口簿的记载,吴某庚是 “1992 年 4 月 30 日,由那琴乡那琴村上伴屯迁来本市 (县)”,即 1978 年至 1992 年间,黄某壬生活在 “那琴村上伴屯 67 号”,吴某庚户曾经在落实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期间承包的田地,除非被集体收回,但不可能是《证明》中记载的 “没有获得山水林某等” 的表述。 四、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驳回吴某甲等人的起诉。 能否取得集体收益的分配资格是以是否具有村某丙成员资格为前提,吴某甲等人的某丙资格未经某己确认,而某丙成员资格认定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故应驳回吴某甲等人诉请。吴某甲等人辩称,某己的请求不能成立。 吴某乙、吴某己、吴某戊的母亲黄某戊是某己的原始村民,吴某乙、吴某己、吴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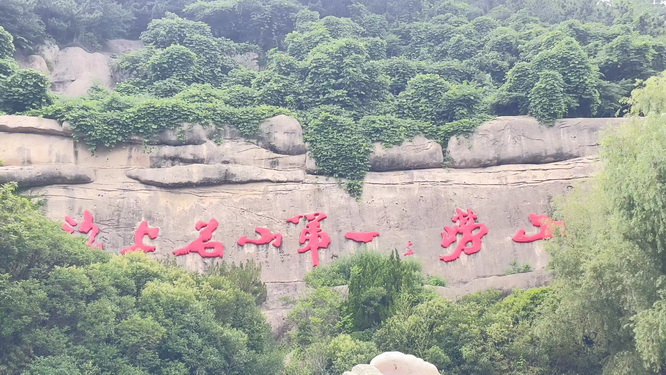 戊自出生后户口就跟黄某辛村民小组,而且还与黄某戊作为农户成员承包了某己土地,四口人形成了加达村民小组的原住村民,至此开始就具有村民小组的资格,不管吴某乙、吴某己、吴某戊的户口是否有变化,但是吴某乙、吴某己、吴某戊的基本情况和加达村民小组给予李某乙、黄某丙、黄某丁等人的待遇跟情况一致。
戊自出生后户口就跟黄某辛村民小组,而且还与黄某戊作为农户成员承包了某己土地,四口人形成了加达村民小组的原住村民,至此开始就具有村民小组的资格,不管吴某乙、吴某己、吴某戊的户口是否有变化,但是吴某乙、吴某己、吴某戊的基本情况和加达村民小组给予李某乙、黄某丙、黄某丁等人的待遇跟情况一致。
二审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某己支付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集体收益款各 6800 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之规定,该条明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指的是因某丙征地补偿费数额提起的民事诉讼,而吴某甲等人是因不能享受与某丙成员同等权益和待遇,起诉要求分配相同的份额,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正确,二审予以确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某丙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某丙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 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某丙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的规定,吴某甲等人主张分配某己的集体经济收益应当以其是否具备某己某丙成员资格为前提,而是否具备农村某丙成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户籍在或者曾经在农村某丙;2、与农村某丙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3、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 本案中,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虽曾落户在某己,但在 1994 年 4 月 1 日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户籍因 “农转非” 从某己随父亲迁入上思县某公司,其户口已由农村转为城镇,且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在户口迁出后仍与某己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积极履行农村某丙成员权利和义务,并以某己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作为其基本生活的保障,故吴某乙、吴某戊、吴某己已不具备某己某丙成员资格。一审判决认定有误,二审予以纠正。 吴某甲、李某甲、吴某丙、吴某丁、黄某甲户籍未落户于某己,且亦无证据表明其与某己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某己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作为其基本生活的保障,一审判决认定吴某甲、李某甲、吴某丙、吴某丁、黄某甲不具备某己的集体经济组织资格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 因吴某甲等人不具备某己的集体经济组织资格,故对于吴某甲等人主张某己向其支付某丙收益,二审不予支持。 吴某甲等人又主张一审法院未查明李某乙、黄某丙、黄某丁等三家农户基本情况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审认为,李某乙、黄某丙、黄某丁等是否具有某己某丙成员资格与吴某甲等人是否具有某己某丙成员资格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未予查明并无不当。 关于案外人黄某戊是否取得吴某庚户所在地上思县那琴乡那琴村上伴屯某丙的承包地,享受吴某庚户所在某丙成员待遇,二审认为黄某戊是否享受吴某庚户所在某丙成员待遇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对申请调查黄某戊是否享受吴某庚户所在某丙成员待遇不予准许并无不当,该上诉主张不成立。
二审判决
二审判决: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吴某丙、吴某甲、黄某甲、吴某戊、李某甲、吴某乙、吴某丁、吴某己的诉讼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