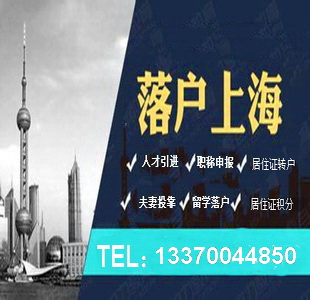结果很明显——整栋楼被认定为严重虫害,嫌疑点锁定在二十五楼那户长期囤垃圾的住户,真让人无语。物业、居委会和相关部门都介入了,消杀频次从每周一次提升到每天一次,结果呢,想要从根儿上解决又碰到不能强行入户的硬性限制。现在楼里的人都不敢正常开窗,保洁员有人已经递了辞职书,矛盾还在发酵。
物业这边是在压力锅里忙着应对。接到投诉后,物业把整幢楼公共区域的消杀升级了,电梯、楼道和垃圾站都加上了消毒和粘虫板。负责这幢楼的李经理说,办公室每天都会接到好几个业主的电话,大家催得很急,"赶紧解决"成了常态。物业没有执法权,不能强行入户,只能尽力清理公共区域,并向社区和住房保障办报备,希望靠部门协调推进。业主有时气得来物业理论,口气很激烈,物业也很尴尬,真是两头为难。
社区也出手了。居委会的王主任说,他们已经联系到25楼住户的亲属,找到了一位姐姐,希望她能回来劝说当事人配合清理与消杀。社区还在和城管、疾控等部门商量对策,目标是在不侵犯业主隐私和产权前提下,找到合法可行的处理路径。社区人员多次上门,也碰到不开门、不接电话的情况,劝说无果。
楼里其他住户的反应相当直接。22楼的张先生花了将近一千元请了专业消杀,效果只是暂时的,过了几天蟑螂又回潮;18楼的王女士则从最初看到一只跑过的蟑螂,发展到家里各处都有,晚上甚至能听到天花板上爬行的声音,生活被彻底打乱,窗户半个月没敢打开,孩子因为长期喷杀虫剂还出现咳嗽、打喷嚏的症状。邻居刘女士每天走过那层楼,都被门口的臭味熏得难受,只能捂着鼻子匆匆走人,emm 真尴尬。
关于二十五楼的具体情况,保洁员和业主给出了不少细节描述。保洁人员说,这家人住了好几年,最近两年倒垃圾的 频率明显下降。物业清洁时常闻到刺鼻异味,夏天尤其严重,工作时不得不戴口罩。门口楼道常见黑色塑料袋,袋子破了,剩饭菜、纸巾露出来,散发酸臭。消防栓上甚至能看到几只死蟑螂,墙角也有爬行留下的痕迹。记者到现场也看到了这些情况:地上有破损的垃圾袋,门口散落着残渣。
频率明显下降。物业清洁时常闻到刺鼻异味,夏天尤其严重,工作时不得不戴口罩。门口楼道常见黑色塑料袋,袋子破了,剩饭菜、纸巾露出来,散发酸臭。消防栓上甚至能看到几只死蟑螂,墙角也有爬行留下的痕迹。记者到现场也看到了这些情况:地上有破损的垃圾袋,门口散落着残渣。
和当事人直接沟通非常困难。物业多次上门被拒,有时隔着门对话,得 到的回答是“家里有事”“不需要物业管”,还有人直接挂断电话。记者打过去也无人接听,短信发出后也没有回复。一次物业带着专业消杀设备上门劝说进入户内消杀,结果被明确拒绝。于是物业只好把情况上报给社区和住房保障办,寻求行政层面的介入。
到的回答是“家里有事”“不需要物业管”,还有人直接挂断电话。记者打过去也无人接听,短信发出后也没有回复。一次物业带着专业消杀设备上门劝说进入户内消杀,结果被明确拒绝。于是物业只好把情况上报给社区和住房保障办,寻求行政层面的介入。
保洁人员承受了很大压力。张阿姨在这栋楼做保洁三年多了,最近已经递交了辞职申请。她负责一到三十层的公共楼道和电梯间,工作量骤增,还要每天额外喷杀虫剂,清理蟑螂尸体。她的手套上有污渍和杀虫剂残留,手指上甚至出现了被虫咬出的小洞。长期处在这种环境,她反映有头晕、恶心,皮肤也出现红肿和瘙痒。其他几位保洁员也想辞职,曾向物业要求调整岗位或提高补贴,但到现在还没看到明确方案。物业表示会增加岗位补贴、改善防护装备,并紧急招聘新的保洁人员,以免出现人员断档。
事情的源头要从更早的观察说起。邻居们发现,一个规律是越靠近25楼,蟑螂越密集。最早发现问题的住户,比如王女士,是在一个月前在厨房看到一只大的蟑螂;张先生则是在衣物上发现了排泄物、咬痕,还有蟑螂卵鞘。居民们私下交流后,开始怀疑二十五楼是问题源头。于是大家把线索告诉了物业,物业做了初步排查,把重点放在25楼这个单元上。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类邻里纠纷涉及到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边界问题。物业能管的是公共区域和服务职责,社区及相关部门有调解和行政手段,但要彻底解决都离不开当事人的配合。现在的状况是多方同时推进:物业加大公共消杀,社区在联系家属,住房保障办也在关注,业主持续投诉,一些住户不得不开窗或改变生活方式以减少接触。大家每天都在和看得见的蟑螂、闻得到的异味打交道。
这个过程中有几个转折点值得留意。最开始,个别家庭发现蟑螂并没有太在意,结果迅速扩散成整栋楼的问题,居民从单一投诉转向集体维权。随后物业在没有入户授权的情况下尽力做公共防治,但效果明显有限。社区介入并找到当事人的亲属作为下一步尝试,但能否说服本人配合还不得而知。保洁队人手紧张又把问题往外推,已经影响到小区整体服务的持续性。
现场的细节反复被提及:门口破损的垃圾袋、楼道的异味、消防栓上的死蟑螂、孩子咳嗽、专业消杀费接近一千元、保洁员的手套和健康问题,这些画面在居民和物业的描述中一再出现。每一处细节都让邻里矛盾更具体,也凸显出行政介入的必要性。到目前为止,既有生活质量被影响的现实问题,也有体制上如何处理私人房产行为的难题在现实中碰撞,emm 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