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一口气生了个女儿,为什么北大教授撒谎说“生了个男孩”?
有时候,家里的喜事反倒需要藏着掖着。你看刘半农,堂堂北大的教授,风风光光书香世家,女儿出生那天,喜悦还没捂热乎,回头对朱惠说:“对外就说咱们算是生了个儿子。”家里明明刚添了个粉雕玉琢的小丫头,他却不能对外招摇;朱惠愣了愣,没多问,反倒笑着点头。你说这世上的规矩,拧巴不拧巴?
咱们慢慢往下捋。
刘半农家里头代代书香,江苏江阴的刘家人,个顶个都是倔强又讲理的老知识分子。他是家里的大儿子,从小活络、伶俐,六岁便能对诗作对,父亲刘宝珊望着这个孩子,巴不得他一飞冲天。其实那时的刘半农,就是个淘气包,别看读书好,淘气起劲也不让家里省心。书倒是读得多,但也没少为喜欢画猫画狗的事儿,被老刘揪了耳朵。
可十几岁的时候,他心里那点儿争争的劲儿,倒真是带了出来。江阴县一年办一次童子试,他拿了个第一。回头家里人请客,邻居大婶摸着他的脸说一句:“半农啊,哪天你要是考不到状元,可别让你爹失望。”这种话听多了,有压力,他还真往心里去了。
1905年,刘半农进了常州府中学堂,这是县里娃都眼巴巴想进的学校。校长叫屠元博,挺有名气的一个学者。刘半农在校里日子不坏,就是有点轴。上厕所、吃饭、睡觉一条龙,别的时间统统用来啃书本。宿舍里有同学说他“书呆子”,可是考试成绩杠杠的,还不是每次都九十多分——成了老师的心头好。
说起来,刘半农进学堂那会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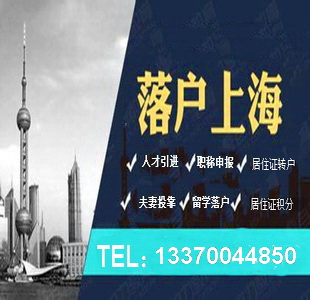 有回去拜访校长,阴差阳错碰见了屠元博的父亲——屠敬山。老爷子是个史学大咖,刘半农其实挺怵的,但那天不知是哪里来的胆气,咧嘴就聊上了。结果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谈得还蛮投机。屠老爷子觉得这孩子脑子够快,能力不马虎,竟开口要收他当关门弟子。刘半农心里踏实、嘴上却连“谢谢师父”都顾不得说顺溜。你别说,要是一般人,早就飘了。
有回去拜访校长,阴差阳错碰见了屠元博的父亲——屠敬山。老爷子是个史学大咖,刘半农其实挺怵的,但那天不知是哪里来的胆气,咧嘴就聊上了。结果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谈得还蛮投机。屠老爷子觉得这孩子脑子够快,能力不马虎,竟开口要收他当关门弟子。刘半农心里踏实、嘴上却连“谢谢师父”都顾不得说顺溜。你别说,要是一般人,早就飘了。
不过,有人眼红就有人嘴碎。学堂里马上有人嚼舌根儿:什么收徒不过是沾了油嘴滑舌,占了“巧劲儿”罢了;说他没两把刷子,全靠溜须拍马。你说气人不气人?但刘半农咬咬牙,心里想:你们看着吧。机缘巧合,知府来视察,出了道作文题,刘半农三下五除二写了篇妙文,结果光荣地拿了第一。当场让一屋子人闭了嘴。
这些小插曲,其实和后面他和朱惠的故事,还有点因果。
再说说刘半农的婚事,不得不提他娘——老李家出来的,虔诚佛教徒,三天两头给家里念经求平安。1910年夏天,她突然病重,临终前咬着牙也得盼着儿子娶媳妇,想冲冲喜。从小朱惠家跟刘家差不多路数,也是讲究规矩会过日子的。那时俩妈妈当庙里碰头,聊着聊着就聊到孩子们身上去。朱母瞄上刘半农是实打实想攀这门亲,觉得自家大女儿朱惠人长得好、脾气温和,是个能过日子的。刘母也是喜欢,带着一份稳妥。
谁知,回去跟刘宝珊一说,老头子顿时皱巴巴的:“大三岁还属相犯冲,不妥。”真是讲究太多,把买卖黄了。朱母急了,赶紧说:“还有小女儿啊!”结果谁能想到,好端端的小丫头突然一病不起,就这么没了。真是世事难料,家里气氛一时哑火。可日子还得到过,人情总要还。朱母含着泪把话说到底,刘母心软,刘宝珊一时也觉不好再拒绝,干脆推船顺水,认了大女儿——朱惠。
有意思的是,封建规矩里“未婚夫妻见不得面”,但刘半农哪里理那一套。他悄悄去朱家,正赶上朱惠在院子洗衣服。小姑娘埋头搓衣裳,突然发现有人盯着自己看,心里砰砰响,脸红得像捡了辣椒。朱惠那双小脚还在纱布里裹着,刘半农回去就跟母亲念叨:“如今这年头,还缠小脚,像什么话!”刘母那天乐了,既欣喜刘半农开窍,又觉得自家儿媳真是命好,两头占了便宜。
老一辈走得急,刘家小两口成了亲。刘半农人的确细腻,他不等事情凑巧,他自己总是往幸福的方向推着。婚后搬去上海,过日子倒是清冷安稳,就是膝下无子。这事儿说轻松也轻松,说沉重也沉重——外人看,刘家这大少爷没个儿子,怎么行?刘宝珊又着急,只差没明说:“要不给你纳房小。”话说出口,刘半农和朱惠心里不是滋味。两口子咬着牙直接搬出老宅,到了上海落户。
话说1916年,朱惠肚子终于有了动静,大伙儿都拍手叫好。奇怪的是,孩子落地,却是个女儿。大清早,刘半农抱着女儿,一阵心疼一阵欢喜。女儿皮肤白净,手指头掐得出水,刘半农逗着逗着笑出声,偏偏这时候他板起了脸:“出门都说生了男孩。”朱惠愣住了,嘴唇动了两次,没说话,片刻后才轻轻点头。这一桩桩、一件件,天大地大的事,说到底还不是怕老人家逼着再“纳妾”这一出?
其实,朱惠懂得多。女儿是她肚皮争气、心里却明白男人家的规矩逼人。她不是没压力,但她心知肚明:这个家只有她和刘半农是真心想好好过日子的。刘半农拿主意排外面那一摊子闲话,无非是想护她周全。可这种日子,不说憋屈也是憋屈。
写到这,有人问:半农不是北大的教授,写文章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女权嘛?是的,他成年后,琢 磨着为什么偏偏“他”这个字既代表男性,也用来指女人,甚至指畜生物件。后来他一咬牙,隔开了“她”“它”,就是想给女人多点体面。这事儿说起来轻巧,背后多少人嗤之以鼻,觉得“新花样”而已。可刘半农偏要顶着时代的“老空心菜”往新里活着。生活中闲人嘴上不落好,文章里却留下一笔,后来人都用。
磨着为什么偏偏“他”这个字既代表男性,也用来指女人,甚至指畜生物件。后来他一咬牙,隔开了“她”“它”,就是想给女人多点体面。这事儿说起来轻巧,背后多少人嗤之以鼻,觉得“新花样”而已。可刘半农偏要顶着时代的“老空心菜”往新里活着。生活中闲人嘴上不落好,文章里却留下一笔,后来人都用。
朱惠和刘半农最终如何?谁又说得准呢?有人说,日子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人说他们苦的时候到底也撑过来了。有人说刘半农英年早逝,留了朱惠独自守着家庭往后半辈子;有人说俩人恩爱,也不过是缘尽于笙歌一世。
我自己倒觉得,朱惠那一声“好,就说生的是男孩”里,有多少无奈、隐忍和体谅,也藏着她对半农奇特的温柔。人间小事,常常就是一家的大事。我们嘴上说着开明、先进,一到家门口,绕不过去的门槛,还是门槛。
想到这,我总忍不住琢磨:倘若你是刘半农,换作今时今日,你会坦然告诉全世界“我家添了个闺女”,还是依然选那个“体面”的谎言?也许历史就是这样拧在一起的吧——一头是时代的河水,一头是我们自己的心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