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不记得,王家村的王大叔?”
对面的李伟夹了一筷子花生米,牙口不太好了,嚼得很慢。他抬起眼皮瞅瞅我,眼神里有点迷茫,像是在一堆旧照片里翻找某张特定的面孔。
“哪个王大叔?”
“灵儿她爹。”
李伟的筷子停在半空,然后慢慢放回碗边。他端起茶杯,吹了吹上面的热气,没说话。
我知道,他想起来了。
有些名字,就像是埋在黄土塬下的种子,平时想不起来,可一旦有人提,那股子夹着土腥味儿的记忆,就一下子破土而出,长满了整个心房。
那年头,我们都一样,十几岁的年纪,背着个帆布包,里面塞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本红宝书,就从北京站上了那趟绿皮火车。
车窗外的景物,从高楼变成平房,从平房变成田野,最后,就只剩下了一望无际的黄土。
我们管那叫“战天斗地”,管自己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白了,就是一群半大的孩子,对未来一无所知,凭着一腔热血,就扎进了那片陌生的土地。
王家村,就是我们的落脚点。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都住在窑洞里,像是一窝一窝的土蜂,嵌在山坡上。
刚到的时候,新鲜感盖过了一切。看什么都稀奇。看老乡用大黑锅烙出来的玉米饼子,看他们赶着毛驴去山下驮水,看那些光屁股的小孩在土坡上滚来滚去。
李伟比我适应得快。他会来事儿,嘴也甜,没几天就跟村里的年轻人混熟了,张口“叔”闭口“婶”的,叫得比谁都亲。
我性子闷,不太会说话,就喜欢一个人闷头干活。队长让干啥就干啥,挑水,锄地,起粪。
手上的泡起了一层又一层,最后磨成了茧子,也就习惯了。
那时候觉得,日子就该是这样过的。白天一身汗,晚上一身土,躺在冰凉的炕上,累得连梦都做不了。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稳定,规律,一眼能望到头。
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城。
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谁也不说,但谁心里都清楚。我们是过客,这里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驿站。
直到那场病的到来。
秋天,玉米收完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凉。我也不知道是着了凉还是吃坏了东西,突然就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发烫。
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是水土不服,扛两天就过去了。
可没想到,越来越重。烧得我迷迷糊糊的,躺在炕上,感觉自己像一块被扔进灶膛里的炭,里里外外都在着火。
李伟他们也慌了。他们把我从知青点带来的那点药都翻了出来,什么感冒片,止泻药,一把一把地往我嘴里塞。
没用。一点用都没有。
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在往下沉,像是要沉到这黄土地的最深处去。
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有人在吵。是李伟的声音,还有村长的声音。
“得送去公社卫生院!再不送人就没了!”李伟的声音带着哭腔。
“几十里山路,怎么送?就他现在这个样子,颠一下就散架了!”村长的大嗓门吼得窑洞嗡嗡响。
“那怎么办?就这么看着?”
后来,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但是很稳。
“我爹说,他有办法。”
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睁开眼,天已经亮了。
窑洞里很安静,只有窗户纸上透进来的光,把屋里的土墙照得一片昏黄。
我感觉嘴里很干,喉咙里像是有火在烧。我试着动了动,才发现自己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你醒了?”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我转过头,看见一个姑娘坐在炕边,手里正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
是灵儿。王大叔的女儿。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条辫子又黑又粗,垂在胸前。她的眼睛很亮,像山泉水洗过的黑石子。
我认识她,但不熟。平时在村里见到,也就点个头。她不像村里别的姑娘,喜欢凑在知青点门口看热闹。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干活,话不多。
“喝点水吧。”她把碗递到我嘴边。
碗里是温热的小米汤,上面飘着一层米油。我闻到那股熟悉的香味,胃里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她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喂我。
我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盖的被子,不是我们知青点那床又薄又硬的行军被,而是厚实柔软的棉花被,上面还带着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
“我……”我张了张嘴,声音哑得像破锣。
“你发高烧,烧了好几天。”灵儿说,“我爹给你刮了痧,又去山上采了草药,给你熬了汤灌下去,才把烧退了。”
我愣住了。
刮痧?草药?这些东西,我在书上见过,但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用在自己身上。
是这些东西,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的?
“谢谢……”我干巴巴地说。
灵儿摇了摇头,没说话,只是低头继续喂我喝米汤。
从那天起,我就住在了王大叔家。
知青点的窑洞太潮,人也多,不利于养病。王大叔做主,把我挪到了他家旁边一间空着的小窑洞里。
每天,灵儿都会准时给我送饭送药。
早晚是小米粥,中午是烂糊的面条。药汤黑乎乎的,苦得人舌头发麻,但她会提前在碗边放一小块红糖。
她不怎么说话,就是默默地做着这一切。收拾我换下来的脏衣服,给我擦身子,倒尿盆。
这些活,又脏又累。可她做起来,却那么自然,脸上没有一丝一毫不耐烦的神情。
我一个北京来的大小伙子,一个自诩要“战天斗地”的知识青年,就这么被一个农村姑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感激,是肯定的。但除了感激,还有一种很陌生的情绪在悄悄发酵。
我开始观察她。
她的手很巧,能用最普通的玉米叶子编出活灵活现的小篮子。她的针线活也好,我的衣服破了洞,她拿过去,没多久就补得整整齐齐,针脚细密得像印上去的。
她还认得山里各种各样的植物。哪种能吃,哪种能入药,她都一清二楚。
在我眼里,她就像这片黄土地一样,看着沉默,却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
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能下地走路了。
李伟他们来看我,带来了公社供销社买的罐头和饼干。
“陈辉,你可算捡回一条命。”李伟拍着我的肩膀,一脸后怕,“那天你烧得都说胡话了,我们都以为……”
他没说下去。
我看着他手里的罐头,再想想灵儿端来的那碗小米粥,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我欠王大叔一家的,不是一个水果罐头能还清的。
我欠的是一条命。
这个认知,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它彻底打破了我之前那种“过客”的心态。
我不再是那个只需要埋头干活,等着回城的知青了。
我跟这个村子,跟这家人,产生了一种无法割裂的联系。
一个伦理上的难题,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摆在了我面前。
我该怎么还这个人情?
病好利索之后,我搬回了知青点。
但我去王大叔家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
一开始,我就是想找点活干,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
王大叔家的水缸,我每天都给挑满。院子里的柴火,我一有空就去劈。地里的活,只要我能帮上手的,绝不推辞。
王大叔是个典型的庄稼汉,话不多,脸上的褶子像黄土塬上的沟壑。他看着我忙前忙后,也不说啥,就是吃饭的时候,会让我媳妇,也就是灵儿她娘,多给我盛一碗饭。
灵儿她娘是个和善的妇人,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小陈,多吃点,看你瘦的。”
只有灵儿,她好像总是在躲着我。
我挑水,她就去喂猪。我劈柴,她就去纳鞋底。我们俩好像总也碰不到一块儿。
有时候在院子里遇上了,她也是低着头,匆匆走过去,脸颊上飞起一抹红云。
村里开始有闲话了。
那些婆姨们,聚在村口的酸枣树下,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拿眼角瞟我,嘴里嘀嘀咕咕的。
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但那眼神,我看得懂。
李伟也找我谈过一次。
那天晚上,我们俩躺在炕上,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陈辉,”他忽然开口,“你最近……跟王家走的有点近啊。”
我“嗯”了一声。
“你可想好了。”李伟坐了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咱们是来插队的,早晚要回城的。你别犯糊涂。”
我心里一沉。
“我没犯糊涂。王大叔救了我的命,我报答他们,不对吗?”
“报答是应该的。”李伟说,“可你这报答法,有点过了。村里人都说,你看上他们家灵儿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别瞎说。”我嘴上反驳,声音却没什么底气。
“是不是瞎说,你自己心里清楚。”李伟叹了口气,“陈辉,我拿你当兄弟才跟你说这些。灵儿是个好姑娘,可她不适合你。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你将来是要回北京,上大学,进工厂的。她呢?她离得开这黄土地吗?你别一时冲动,害了人家姑娘,也耽误了你自己。”
李伟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对。
理智上,我完全明白。可情感上,我却控制不住自己。
我控制不住自己想去王大叔家,控制不住自己想看到灵儿。哪怕只是看一眼她低头编篮子的侧影,心里就觉得踏实。
那段时间,我特别矛盾。
白天,我拼命地干活,想用体力上的疲惫来麻痹自己。
晚上,躺在炕上,李伟的话就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响。
回北京。
这个念头,曾经是我们所有知青的支撑。可现在,它对我来说,却变得有些模糊了。
我眼前浮现的,不再是北京的高楼大厦,而是王家窑洞前那昏黄的灯光,是灵儿递过来那碗小米粥时,低垂的眼帘。
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不理智的决定。
我不想再这么不清不楚下去了。我要给自己,也给灵儿一个交代。
我跟队长申请,说我想学着编席子。
我们这里产芦苇,村里有几个老师傅会编芦苇席,这是个技术活,也是个重要的副业。
队长挺意外,但看我态度坚决,就同意了。
教我技术的,是村里的一个老人,大家都叫他三爷爷。
三爷爷的手艺远近闻名,但他脾气古怪,一般不收徒弟。
我去拜师的时候,他正坐在院子里,慢悠悠地撕着芦苇。他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问我:“城里娃,吃得了这个苦?”
“吃得了。”我答得斩钉截铁。
编席子,看着简单,其实全是功夫。
芦苇要一根一根地撕,撕得粗细均匀。手指头很快就被磨破了,钻心地疼。
经线要绷得紧,纬线要穿得密。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眼睛都花了。
头一个月,我编出来的席子,歪歪扭扭,跟狗啃过一样。
李伟他们都笑我,说我放着好好的农活不干,非要干这个,不是自讨苦吃吗?
我不理他们。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三爷爷家。他干活,我就在旁边看着,学着。他休息,我就帮他扫地,挑水。
三爷爷不怎么说话,但他看我的眼神,慢慢变了。
有一天,他指着我手上缠着的布条,问:“还疼?”
我摇摇头:“习惯了。”
他点点头,从屋里拿出一卷新的席子,铺在地上。
“你看看这个。”
那张席子,编得又光又滑,平整得像一块布。上面的花纹,是两只喜鹊,活灵活现的。
“这叫喜鹊登梅。”三爷爷说,“是婚嫁用的。”
我看着那席子,心里一动。
“三爷爷,您能教我编这个吗?”
他看了我很久,才缓缓地说:“你要是真想学,就用心学。”
从那天起,三爷爷才算是真正开始教我。
他把所有的诀窍,都一点一点地传给了我。怎么选料,怎么浸泡,怎么起头,怎么收尾。
我学得很用心。
手上的伤好了又破,破了又好。到了冬天,天寒地冻的,泡芦苇的水冰得刺骨,我的手生满了冻疮,又疼又痒。
可我没停下。
因为我心里有个念想。
我要编一张最好看的喜鹊登梅,送给灵儿。
这个念头,像一团火,在我心里烧着,让我忘了所有的苦和累。
我不再去想回城的事,也不再去管别人的闲话。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了那些芦苇,和那张越来越成形的席子。
我的心思,从“我该怎么办”,变成了“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她明白我的心意”。
我不再被动地承受着命运的安排,而是开始主动地,为自己的内心,做出一个选择。
春节前,那张“喜鹊登梅”的席子,终于编好了。
我把它卷起来,用红绳子捆好,心里又激动又忐忑。
我不知道灵儿会不会收,也不知道王大叔会是什么态度。
我抱着那卷席子,在王大叔家门口徘徊了很久,才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那天,王大叔一家人都在。
我把席子放在炕上,解开红绳,慢慢展开。
窑洞里的光线很暗,但那两只喜鹊,却像是要从席子里飞出来一样。
灵儿她娘“哎呀”了一声,眼睛都亮了。
灵儿也愣住了,她看着那席子,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王大叔一直没说话。他盘腿坐在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开口了。
“王大叔,婶子……我……我喜欢灵儿。我想娶她。”
话说出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窑洞里,一下子静得可怕。只剩下王大叔抽烟的声音,和炕上那只老猫的呼噜声。
过了很久,王大叔才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
他抬起头,看着我。
他的眼神,很平静,但又像是一口深井,能把人吸进去。
“陈辉,”他开口了,声音很沉,“你是个好娃。你病的时候,我们救你,不是图你报答。”
“我知道。”我赶紧说,“我是真心的。”
“真心?”王大叔笑了笑,那笑容里,却没什么笑意,“你的真心,值几个钱?”
我愣住了。
“你是个城里娃,是吃公家粮的。我们灵儿,是个农村丫头,是土里刨食的。你们俩,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我可 以不回城!”我急了,“我可以把户口迁过来,就在这儿落户!”
以不回城!”我急了,“我可以把户口迁过来,就在这儿落户!”
王大叔摇了摇头。
“你说得轻巧。现在政策是这样,谁知道以后会怎么变?万一哪天,政策松了,你们知青都能回城了,你怎么办?”
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到时候,你是带着灵儿走,还是把她一个人扔在这儿?”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攥住了。
“你带着她走,她一个农村丫头,到了你们北京城,人生地不熟的,她能过得惯吗?她认识谁?谁又认识她?她受了委屈,能跟谁说?”
“你要是把她扔在这儿,她算什么?一个被城里人甩了的女人,以后还怎么嫁人?村里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
王大叔的话,像一把一把的刀子,扎在我的心上。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
我以为,只要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就够了。
可我忘了,这不是两个人的事。这是两个家庭,两个世界的事。
“大叔……”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所有的决心和勇气,在他这几句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话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就在这时,一封信,彻底把我打入了谷底。
是李伟从公社取回来的,我妈写的信。
信里,我妈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口吻,问我是不是在农村谈了对象。她说,她听别的知青家长说的,心里很不安。
她求我,千万不要犯糊涂。
她说,家里一切都好,爸爸的身体也还硬朗,他们都在等我回家。
她说,我的未来在北京,不在那个穷山沟里。
信的最后,那张薄薄的信纸上,有几处模糊的印记。我知道,那是我妈的眼泪。
我拿着那封信,坐在窑洞的土炕上,从天亮坐到天黑。
一边,是王大叔那几句戳心窝子的话。
另一边,是我妈那滴着眼泪的期盼。
我感觉自己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
我珍视的一切,我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我对爱情的执着,我对我父母的承诺,在这一刻,好像都崩塌了。
我该怎么办?
我好像,被推到了一个绝望的悬崖边上。
那几天,我像个丢了魂的木偶。
白天照常出工,但脑子里空空的,别人跟我说话,我得反应半天才能听进去。
我不敢去王大叔家,也不敢见灵儿。
我怕看到她那双清澈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我给不起的未来。
李伟看我这样,也替我难受。他不再劝我,只是默默地把我的那份饭打好,把我的水壶灌满。
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憋得受不了,一个人跑到了村后的山坡上。
夜很深,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黑得让人心里发慌。
我就那么坐着,看着山下村子里零零星星的灯火。
王大叔家的那点光,在黑暗中,显得特别温暖。
我想起了我刚来的时候,也是坐在这里,看着同样的景象。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这些灯火,都与我无关。
可现在,我知道,有一盏灯,是为我亮过的。
我想起了我发高烧,人事不省的时候,是王大叔用土方子把我救了回来。
我想起了灵儿,一勺一勺地喂我喝小米粥,给我换洗缝补。
我想起了三爷爷,手把手地教我编席子,把冻伤的药膏塞到我手里。
这个村子,这片土地,这些人,他们用最朴实的方式,接纳了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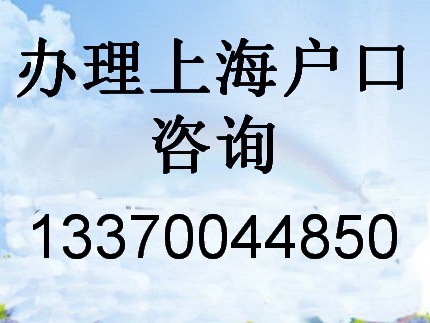 拯救了我。
拯救了我。
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而我,却在考虑要不要抛下他们,回到我原来的世界去。
王大叔问我的那些话,又在我耳边响起。
“你是带着灵儿走,还是把她一个人扔在这儿?”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或者B。
可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王大叔他不是在让我选。
他是在考验我。
他考验的,不是我有多爱灵儿,而是我有没有勇气,去承担这份爱背后的责任。
他要看的,不是我的承诺,而是我的决心。
一个真正的男人,不是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
我一直以来,都在逃避。
我嘴上说着要留下,心里却还给自己留着一条回城的退路。
我想要爱情,又舍不得北京的未来。
我什么都想要,结果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就想通了。
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什么都占着。你总得选一条路,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下去。
选择,就意味着放弃。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忽然就落了地。
我不再纠结,不再犹豫。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天亮的时候,我从山坡上下来,直接走到了村长家。
村长正蹲在院子里吃早饭,一碗玉米糊糊,一碟咸菜。
看到我,他有点意外。
“陈辉?这么早,有事?”
我站在他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村长,我想好了。我要在王家村落户。请您帮我办手续。”
村长手里的碗顿住了,他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我,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你……你说啥?”
“我说,我要把我的户口,从北京迁到咱们村。”我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我不当知青了,我要当咱们村的村民。”
在那个年代,把城市户口迁到农村,无异于一场人生的豪赌。
这意味着,我放弃了回城的一切可能。放弃了商品粮,放弃了父母安排好的工作,放弃了那个我生活了十几年的世界。
村长看着我,看了足足有五分钟。
他把碗放到地上,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
“娃,你想清楚了?这不是闹着玩的。手续一办,就没法回头了。”
“我想清楚了。”我看着他的眼睛,目光没有一丝闪躲,“比什么时候都清楚。”
村长没再说话。他转身回了屋,拿出纸和笔,又找出村委会的公章,在上面哈了一口气。
“行。我给你写证明。”
我拿着那张盖着红章的证明,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王大叔家。
他们一家人也正在吃饭。
我走进去,把那张纸,轻轻地放在了炕桌上。
王大叔拿起那张纸,凑到油灯下,眯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灵儿她娘和灵儿,都紧张地看着他。
窑洞里,安静得能听到心跳。
王大叔看完了。
他把那张纸,小心地叠好,揣进了怀里。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
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他冲着灶房喊了一声:“老婆子,去,把炕底下那坛酒拿出来。”
他又转向灵儿,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和。
“丫头,去,给你陈辉哥,下碗面条。记得,卧两个荷包蛋。”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我没有回北京。
我的户口,留在了王家村。我的名字,写进了王家的户口本。
我和灵儿的婚礼,办得很简单。
没有鞭炮,没有酒席。就是请村里几个关系好的长辈,在王大叔家的窑洞里,吃了顿便饭。
我穿着一身洗干净的旧衣服,灵儿穿着她自己做的一件红布褂子。
我们俩,对着墙上那张伟人像,鞠了三个躬。
就算礼成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炕上,谁也没说话。
窑洞里,红色的剪纸贴在窗户上,油灯的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灵儿显得有些局促,两只手不停地绞着衣角。
我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因为常年干活,有些粗糙,但很温暖。
“灵儿,”我看着她,“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她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红到了耳根。她低下头,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一刻,我心里特别踏实。
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了家,有了牵挂。
婚后的日子,平淡,但很安稳。
我不再是知青,而是王家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我跟着王大叔,学着侍弄庄稼。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收割。
我看天色,辨别风向。我用最原始的农具,耕耘着这片养育我的土地。
一开始,我干活还是不行,笨手笨脚的。
但我不怕。我肯下力气,肯学。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渐渐变了。
他们不再把我当成一个随时会走的“城里娃”,而是真正把我当成了自己人。
他们会跟我开玩笑,会把自家种的菜塞给我,会教我怎么用柳条编筐。
灵儿是个好媳妇。
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的每一件衣服,她都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
每天我从地里回来,她都给我备好了热水和热饭。
我们话不多,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彼此就都懂了。
有时候,晚上我们俩会坐在窑洞门口,看天上的星星。
陕北的夜空,特别干净,星星又多又亮,像是撒了一把碎钻。
灵儿会靠在我的肩膀上,跟我说她小时候的故事。说她怎么跟着她爹去山上采药,怎么在河里摸鱼。
我听着,心里就觉得特别安宁。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简单,真实,有温度。
后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
村里的知青们,都沸腾了。
他们一个个都像是打了鸡血,没日没夜地翻着从箱子底找出来的课本。
李伟也来找我。
“陈辉,这是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一起考,一起回北京!”他抓着我的胳膊,眼睛里放着光。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
“我不考了。”
李伟愣住了。
“为什么?你疯了?这是咱们等了多少年的机会啊!”
我笑了笑,指了指院子里。
灵儿正挺着大肚子,在院子里晒着尿布。阳光照在她身上,整个人都像是在发光。
“我的家在这儿。”我说。
李伟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他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明白了。你……保重。”
那年冬天,知青们陆陆续续都走了。
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被招工回了城。
知青点,一下子就空了。
我去送李伟。
在长途汽车站,他紧紧地抱了我一下。
“陈辉,以后常联系。”
“一定。”
车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他趴在车窗上,冲我使劲地挥手,眼圈红了。
我知道,我们这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第二年春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王大叔抱着自己的外孙,笑得合不拢嘴。他给孩子取名叫“念祖”,意思是,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再后来,改革开放了。
村里也慢慢有了变化。
通路了,通电了。有人开始在外面做生意,盖起了砖瓦房。
我也没闲着。
我把我当年跟三爷爷学的手艺捡了起来。我带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编芦苇席。
我改良了花样,还托人联系到了县里的供销社,打开了销路。
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我们从窑洞搬进了新盖的砖房。儿子也长大了,去县里上了最好的中学。
他很争气,后来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
毕业后,他留在了西安工作,娶妻生子。
他好几次想接我和灵儿去城里住,说城里条件好,医疗也方便。
我们都拒绝了。
我们离不开这片黄土地。
我们的根,在这里。
……
“后来呢?”
李伟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后来?后来王大叔和婶子都走了。灵儿前几年也走了。”我平静地说。
李伟的眼神黯淡了一下。
“那你……”
“我还在村里住着。儿子每个月都回来看我。挺好的。”
我们俩都沉默了。
饭店里人声鼎沸,可我们这一桌,却安静得像是另一个世界。
过了很久,李伟才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陈辉,这么多年,你后悔过吗?”
我看着他。
他头发白了,脸上有了老年斑,眼角的皱纹,比当年王大叔的还要深。
他回城后,进了不错的单位,当了不大不小的领导,儿女也都很有出息。
从世俗的眼光看,他比我成功得多。
我笑了笑。
“后悔什么?”
我反问他。
“后悔没回北京?还是后悔没上大学?”
我摇了摇头。
“李伟,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当年那个决定。”
“那片黄土地,它拿走了我的青春,却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一个爱人,给了我一个儿子。它让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它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什么是爱。”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
“那段在陕北插队落户的经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因为在那里,我找到了我的根。
















